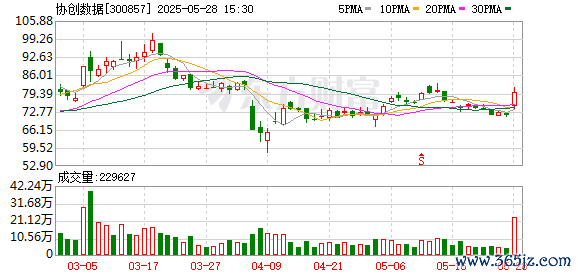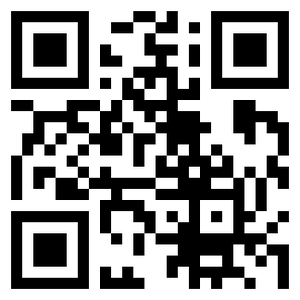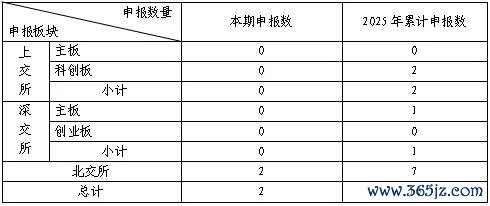01配资网站
“娘啊!”
2003年那个寒风刺骨、雪花漫天飞舞的冬夜,老屋里突然响起一个男人沉重而悲痛的哭喊声。不一会儿,另一名男子也跟着放声大哭,哭声更为凄厉撕心。爷爷去世已整整七年,奶奶也终于离开了我们。
第二天还得上学,本已入睡的我被楼上传来的哭声惊醒。那沉闷而撕心裂肺的哭声,是我的父亲发出的,他是个朴实无华的庄稼汉。紧接着传来的凄厉喊叫,则是来自我的伯父——一个长期奔波于苏皖地区的小商人。
母亲急切地催促我穿衣下楼,几个月来一直担忧的事终于发生了,但事情真真落地时,心中的害怕反倒减轻了些。站在奶奶的病床前,父亲、伯父、伯母和三个姑妈都在场。二姑妈则低声在门口给远方亲戚打电话,叮嘱他们天亮就赶回来。
屋内的女眷们沉默寡言,站在奶奶那形容枯槁的身躯旁,她的女儿们满脸哀伤。两个儿子则泪如雨下。我看着奶奶那张干瘪的脸,握住她像枯树枝般干裂的手,鼻头一阵酸楚,眼泪却硬是流不出来。
展开剩余88%母亲帮我向村小老师请了整整一周的假期,奶奶的葬礼迅速展开。
女眷们表面上似乎有说有笑,男丁们则一个个喝得脸红耳赤,吹牛拍马,似乎异常欢乐。如果不是屋里贴着白色的哀联和地上散落的纸钱,这一场景和我参加过的喜宴几乎没两样。我鼻尖一阵酸涩,眼泪再也止不住。
后来长大回想这些情景,活着的人该吃吃喝喝、该欢乐,或许这就是成人看待死亡的方式。但我心里始终五味杂陈——到底是来吊唁,还是来吃酒席的呢?
饭菜上得差不多,摩托车、皮卡和小面包发动了,人们陆续离去,老屋渐渐恢复寂静,院子里散落着杯盘狼藉。我以为这场令我不快的葬礼就此结束,却没想到,这竟是家庭纷争的序幕。
02
我落寞地回到自己的房间,正准备收拾书包迎接第二天的学校生活,忽然楼下传来碗碟碰撞破碎的声音。我急忙走出房间,靠在栏杆上往下看,竟见大伯和父亲扭打在草地上翻滚,不知是谁跌倒时把一桌子的碗碟撞翻了,我吓得急忙跑下楼去。
大伯那胖乎乎的小个子很快被我那质朴的父亲按倒在地,急促地骂着父亲的名字。令人惊讶的是,在场的几位长辈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手干预,尤其是三叔公,他竟然坐在一旁拍手叫好,好像在期待他们打出个输赢。
大伯头发上沾满了紫菜叶子和鸡蛋花,看来撞翻整桌饭菜被浇了蛋花汤的正是他。
看见越来越多的人围拢过来,俩人忽然默契地停手,父亲从大伯身上站起,大伯揉着腰,扒拉掉头上的菜叶,气鼓鼓地回屋换衣服去了。
当天晚上,大家又摆出一桌饭菜,请来了村里的两个德高望重的老人,大伯、父亲和三个姑妈坐下来商谈几日来的开销及老宅的分配问题。
按传统习俗,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,三个姑妈对遗产毫无挂念,主动放弃分割权,也不承担两万多的丧事费用,结果是父亲和大伯各自负担一半。
爷爷奶奶都走了,留下的两层六间老屋,楼上是住人,楼下是厨房。奶奶生前吩咐,四间归我父亲,两间归大伯。
或许有人觉得这偏心,但村里人都知道,大伯早年在外经商,城里拥有多处房产,平时很少回村。
爷爷去世后,奶奶与我们一家同住。大伯曾试图让奶奶到城里居住,但老太太很快闹着要回村,因为城里无亲无故,孤单寂寞,还时常与伯母发生矛盾,让大伯难以为继。
奶奶回村后身体每况愈下,最后一年半几乎卧床不起。赡养费用由大伯和父亲平分,姑妈们偶尔探望,留下几百元。
长大后我才听说一句俗话:“久病床前无孝子。”父母日夜操劳,换洗床单、擦拭身体、翻身、喂饭,几乎崩溃。
我明白大人和我对奶奶离世的感受截然不同。我失去了深爱的亲人,而他们失去了沉重的负担。随着时间推移,我愈发理解生命的真谛:活着不必过长,但结束时应轻松些。
三叔公是当晚遗产分配会议的主持,几年后醉酒去世,虽令人惋惜,但我觉得他很幸运,没遭受长期病痛折磨。很多老人病痛缠身,躺床十年二十年,生不如死,这种长寿反倒是一种残酷的折磨。
那晚,除了两个悲痛欲绝的儿子,其他亲人似乎都坦然接受,甚至长舒一口气,仿佛卸下了沉重的负担。
爷爷生前没分配老屋,他精打细算,想平分给大伯和父亲,各三间,但必须在奶奶去世后才可分。
奶奶却改变了计划,她认为大伯在城里已有多处房产,分得村里的老屋不公平。大伯经商成功,父亲留村务农,照顾她理应多分。她甚至觉得大伯应一间不分。
我清楚记得,大伯因听到这话一年前摔门而去。奶奶临终时,大伯默许哥哥得两间,四间留给弟弟。
葬礼结束后,大伯反悔,坚持平分。哥哥和弟弟因此争执扭打。表面上握手言和,实际上仍不认可奶奶的安排。
大伯提起自己多年来寄钱,甚至说到给我压岁钱,暗含指责父亲照顾奶奶没吃亏,反而赚钱。
父亲反应迟钝,母亲却听出话中刺,愤怒反驳,说一年半来照顾老人多辛苦,夫妻俩因此不能务工,若照顾老人能赚钱,为何把奶奶送回村,自己却急着离开?
大伯和伯母面露尴尬,欲言又止。母亲一番强烈回击赢得长辈们支持。大家认为爷爷未料及养老分配,财产在奶奶名下,应按她遗愿执行。照顾老人艰辛外人难体会,理应多分。
虽长辈见证分配,父亲获四间房,大伯心结难解,十五年来拒绝往来,属于他的两间房也一直上锁无人打开。
这十五年,我逐渐明白大伯的心结,也懂得他当年坚持平分的原因。
03
原来,大伯和父亲小时候,还有三个姐姐,家中五口人,生活异常艰难。大伯本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,却在初中不久辍学打工。
大伯靠自己十四五岁起四处打工、当学徒、摆地摊积攒资本,才有了今日成就。他将唯一的读书机会让给了父亲,但父亲高中时贪玩,既未考上分配工作专科,也未进入名牌大学,最终成为村里学历最高的农民。
经历失败后,父亲变得沉默寡言,大伯则更痛恨弟弟辜负家人期望。具体隐情难以得知。
在老屋分配上,大伯觉得自己尽了赡养义务,理应平分。村里人却对这说三道四,质疑他为何只得两间房。
多年来,村中议论不断,父亲生活困苦,邻里投以同情;大伯富有,却被指冷漠,兄弟反目,亲情渐远。
我渐渐理解大伯,毕竟当我离开村庄见过外面世界后,回到村里也觉得格格不入。“哎呦,大学生了?赚多少钱?不如我儿子呢!”“大学生多了去了,也不是什么名牌学校,哼!”
就在我以为两家会彻底决裂时,去年邻居翻盖新房,占用了我家的宅基地。事情复杂,村干部也无力解决。父亲为此与邻居争执,被推倒受伤。
我急忙赶去,邻居变脸叫嚣:“你个娃娃懂个啥!”人穷气短,我家人被压制,无力反驳。
正当父亲准备忍气吞声时,大伯得知消息开车赶回,直奔村委会,带来几位退休生产队干部,拿出旧宅基地资料,对邻居一一说明边界。
邻居爷爷也不得不服气,村干部依据资料教育邻居,最终邻居败诉,拆除浇筑模具,填平地基。
大伯叉腰倚在车盖上指挥工人收尾,离开时仅对父亲点头微笑。兄弟间十五年的隔阂仍未化解。
经历此事,我见识了大伯虽精明且斤斤计较,但并非冷酷。他和父亲因遗产产生的争执,其实只是生活的一面镜子。若我是父亲,或许会爽快接受对半分。
但我知道,事后诸葛亮无用,父母当时的处境才是真正难题。大伯这次出手相助,让我看到兄弟情谊修复的希望。
于是我主动提着礼物拜访大伯一家,受到了热情接待。虽然大伯依旧不与父亲言语,但对我总是亲切招呼,我和堂哥的关系也很好。
起初父母反对,担心我自讨没趣,但几年下来,他们默许我代表家族释放善意,缓和两家关系。
我相信,大伯和父亲终将和解,真正成为亲兄弟,在家族面前和睦相处的那一天不会遥远。
那些长辈难以突破的心结,何不让我们晚辈来尝试打开?
父亲曾感慨地对我说:
“上一代兄弟的恩怨配资网站,没耽误你们这代的感情,你们比我们做得更好!”
发布于:天津市和兴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